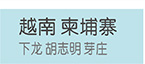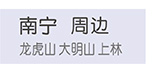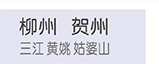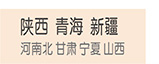在澳大利亚移民从爱尔兰到1973年,我妈妈一直着迷于探索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尘土飞扬的英寸,所以每个圣诞节她会加载所有我们八个孩子进汽车,前往一些遥远和偏远角落的地图。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在夏天我们将游行的范是作为饲料传递当地人交谈。 “没有我们不是一个歌唱剧团”,我妹妹海伦可以解释。 “是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妈妈回答。 “我可以回家了吗? “我会问。 但是,妈妈的信用,她从不放弃。 每年我们会朝着一个不同的目的地,每年货车将过热和每年所有八个孩子就会抱怨的。
当我遇到我的笨拙的青少年时期,这些家庭假日也从轻微不舒服到完全令人尴尬的。 没有一个青少年喜欢被人看到与他们的父母当他们在
假日,但当你的家人看起来像一个爱尔兰版本的冯·特拉普家庭歌手尴尬是混合的。 当你的家人已经一手一个小镇的人口翻了一番很难逃脱的审查。
所有这些来到一头有一年,我的妈妈带我们去在一个废弃的修道院度过圣诞节的海岸附近。 修道院是由一位退休的修道士的照顾他曾不可逆的神经紧张的做上帝的工作在南美丛林中,看到了看守的角色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休息的机会。 然后我的家人到达。
圣诞节已经进入我的家庭的民间传说,这个故事已经被无数次我不容易区分事实与传说。 但我确实记得一个奇怪的足球形状的洞的大型染色玻璃窗口,神秘的出现后的第二天,我们到达。 我也有强烈的回忆的未解决的火,造成气体烧烤和绿廊。 并且,尽管她否认,我敢肯定这是妈妈谁玩温控器的工业冰箱,它导致了破坏的城镇“车轮上的餐饮”圣诞晚餐。 而我的哥哥约翰喜欢完成这个故事说我们被赶出家乡由pitchfork挥舞当地人,我敢肯定我们就知道是时候去当救护车来到采取临时离开一个“休息”。 明年的妈妈开始一个新的传统,在家里举办圣诞。
通过我的20年代,圣诞节已经演变成一个低调,断裂的事情,我的时间划分为我的家人和苏茜的家人州际。 几年后我们试着“一年你的家庭一年我的模型,已经为夫妻忠实地几个世纪以来,但是一旦我们有孩子这个模型变得更难坚持:看起来有一些神圣的权利,是给予他们赋予祖父母,看他们的孙子们在圣诞节。 虽然我很高兴一边吃午餐和晚餐的
澳大利亚,这个速度的旅行并强大的事情要孩子。 添加到这个混合兴奋的圣诞节,一个早期开始,一顿丰盛的午餐,空中旅行,其原因也不难理解你的小天使变成尖叫女妖的烛光Darryl Sommers介绍颂歌。 很明显,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中间立场。
所以几年前苏茜和我决定重新控制了圣诞节。 我们订了一间房子在一个小的海滨小镇,告诉我们各自的家庭他们欢迎访问我们在圣诞节。 那一年苏茜的父母来,呆了一个晚上。 第二年我们回到相同的城镇和苏茜的父母租了一个房子的路上。 同时,我的几个兄弟姐妹租来的房子在该地区,我们有圣诞晚餐在公园里俯瞰大海。 去年,不仅是城镇被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但是囤积苏茜的哥哥和姐姐已经加入了战斗。 包括我们最新的到来,三个新的婴儿将添加到数字今年。 在最近的一次统计,使41圣诞晚餐。
虽然我仍未完全习惯的关注被部分的大家庭的一个小镇,我有我的尴尬交易为家庭的骄傲。 很高兴坐在沙滩上,看着我的女孩玩他们的团队的表亲,知道他们将共享相同的圣诞节的美好回忆。
也有一些独特的放松的事知道,如果我有一个短暂的打盹儿遮阳伞下,至少有一打父母保持警惕在我的女孩。 事实上,它是如此放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们应该邀请一个特定的退休的和尚来与我们分享的圣诞节。